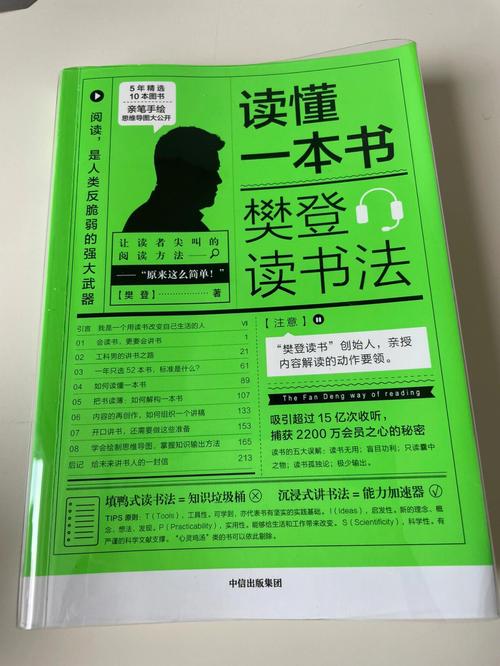醉翁
作践自己,伤害岁月。
那年,我也就八岁吧!和爷爷住在一起,已记不清那时的生活,只隐约记着爷爷嘴里说过的所谓的什么“四书五经”呀,又是什么“秀才举人”啊这些东西。村子里有一个人的形象,至今印在我的脑海和心底;爷爷已经不在了,那个人却时时跑来我的记忆中。
许多年以前,村子里有一个天天喝得烂醉、穿得破烂的人,人家都叫他“醉翁”。醉翁是单身汉,又懒又脏,没人瞧得起他。
我记事以来,就跟着爷爷在村子里“游逛”。有时候,去小卖部打打工,当伙计整点零头。掌柜嫌弃我嘴不够甜,考虑到每天要看别人的脸色,后来便把我给辞退了。
那是一个冬天,北风呼啸,像一个野狼在叫,冷得让人瑟瑟发抖。我在小卖部里打扫卫生,掌柜的嫌我扫得不干净,便打骂我:“什么娘养的……”这话刚放下不久,门外醉翁拄着一根棍子朝着柜台走来,只见他穿着油麻麻的短袄,脸像生锈一样,嘴角没有一丝笑意……语重心长又似乎很没力气的说:“她还是个孩子,怎么能这样打骂她呢?爱自己的孩子是人,爱别人的孩子是神……”他的嘴里还持续嘟囔着很多话语,我也听不懂什么是神,什么者乎,什么怎么样;我只知道醉翁向着我。
这话一出口,掌柜的立即变了脸色,对醉翁说:“哎哟!老爷,您来了;我再也不骂她了;老爷,您今天要点什么?”“老样子。”掌柜的向我使了使眼色,我便麻溜溜地放下扫帚,拿起一瓶二锅头去温一下。醉翁很怪,从未见他买饭买菜,只是单纯的买些酒。有时候会就地喝下,我偷偷地递给他几粒花生米,他就笑笑说:“好孩子……以后甭给我,你掌柜的看见了,会骂你的。”有时候便一把接过来塞在腰包里,一边走一边喝。
村里愣子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举人,但到了愣子这一代,家境衰败了,但愣子天天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挂在嘴上……若是愣子和醉翁一见面,空气中准会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。
这不,“举人”来了。醉翁一气喝下了瓶子里剩下的酒,说:“二愣子,你别能,早晚有一天,我也能考上举人。”
二愣子说:“等你考上举人,地球也就会流泪了。”
一阵笑声扑耳朵而来,唯有我没笑。不久,醉翁把另一瓶二锅头塞进了腰包里,对掌柜的说:“先记账上,19文。”
他离开之后,小卖部里的人来来往往一停不停,有来聊天的,有来买酒的,也有碰巧路过的……
“醉翁又在街上大喊大叫了!”来买茴香豆的人说。出来一看,果真醉翁手里的二锅头已经不多了。他嘴里在嚷嚷着很多我不懂的东西,什么考试,又什么对联,又什么知乎。
晚上打烊回家,只听爷爷说:“醉翁从不吃饭,光喝酒,孤零零地一个人。”我追问:“那他的家人呢?”
“他有个老哥哥,上有老下有小,他又不成器,没人愿意多养一张嘴。”爷爷叹了一口气说。
“那他的工作呢?”
“他一生热爱文学,尤其软笔书法,早先的时候,他给整个村子里的人写对联;他当过医生,他当过老师,他也当过电工;可是他懒到了极点,他只靠捡一些破烂来喝几口小酒。所谓考试,他参加数多次了,一次也没通过。”我为此深感可惜。
之后的日子,我被掌柜的辞掉了,很少与醉翁接触了。
有一年初冬,我和爷爷去集市上卖东西,路过那个大水沟,我们见到了醉翁的最后一面;他掉进了水沟了,看样子已经在水里泡了好几天了。尸体已经冻僵了,皮肤犹如黑炭,短袄破得不成样子,一张瘦条脸上,栽着一些很不稠密的胡须,身板有些单薄,皱纹间夹些伤痕,紫色的脸……
醉翁带着二锅头、所有人的嘲笑、所爱的文字,去追寻一份本应有的平凡。
方下中学九年级二班 王雪慧(指导教师:蔺青春)